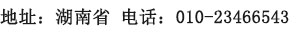学术论衡
你还相信清人版本鉴定?古籍版本杂谈
小马哥/图文阅读古籍,不可避免的要接触点校本,可能和大多数同学一样,我自己也喜欢用点校本,一是字清楚、看着方便,虽然偶有标点疏误,但至少引文起止标清楚,省去了翻检之功,很适合我这种急性子;二是影印古籍的质量通常达不到令人赏心悦目的程度。理想的古籍影印标准应该是宋元存真、明清可读,达不到这种效果,还不如看电子版。(比如某大型古籍汇刊,印的并不尽如人意,其实借鉴国外某些图书馆的做法,直接将善本古籍全彩扫描上网公布,岂不快哉?再说一部部头不大影印善本就要成千上万,买不起我会说吗?呵呵~~)
点校古籍,就要面对不同的版本,更需要在不同的版本之间,选择好恰当的底本。大家都知道,一条好的校记,应该要体现出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,而改字更需要版本依据。在宋元本古籍的点校整理作品中,通常点校者会写类似“某字,原作某,据某某本改”的校记,我们一般也习以为常,认为一条校记本来就应该这么写。其实,作为版本“研究者”,更为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对这部书版本的认识,看他对各种版本的定性,看他能否理清版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先后继承关系。一从这个角度来看,大部分校记离我们心目中理想的校记还有不小的距离。所以说,作为古籍刻本到点校本之间桥梁的点校者,应当对版本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,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点校本的可靠程度。以今日学界之版本水平,把明版、甚至清版古籍误认为宋元版的情况已经不大可能发生,但是仍存在一些版本理论与知识,可能为研究者所忽视。
“SPSS”不可靠
比如说,在清理一部古籍的版本源流过程中,准确确定某些版本的底本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。可能有人说,对比一下,看看异文差异,不是很容易弄清楚吗?可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容易。记得几年前,刚接触版本的时候,有一次去图书馆学习统计软件SPSS,主讲老师特意讲了一个涉及古籍的应用例证,具体记不太清楚了,总之听了以后热血沸腾,感觉版本鉴定终于也可以走上“科学”的道路了:假如有一天,古籍数字化瞬息可成,比较几部古籍版本,之需将其全部文本数字化,然后用SPSS分析,看哪几部相似文本最多,那就是有继承关系了!后来我迫不及待的将其告诉我的老师,老师只是肯定的说还是对比特殊情况最可靠。沮丧而归,一时也没想清楚,直到后来自己有机会参加某古籍的整理工作,需要确定某些版本的来源,才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比如说,学文史的都知道的清殿本《汉书》,要是光对比整体文本,肯定和南宋庆元本《汉书》文字相近,可是殿本刻书跋语明确写道,殿本是以明北监本为底本、再参考庆元本改成的。也就是说,殿本的主体是明北监本,对比某些特殊的错字,一目了然,只是再根据别的依据改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再如清代张敦仁刻之《仪礼注疏》,光看整体文本的话,疏文部分自然和单疏本很相近,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其是用明末毛晋刻本为刊刻底本,只不过疏文部分是根据单疏校本改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。类似情况,在古籍刊刻过程中很普遍,所以单纯根据文字相似比率不能确定版本源流。相较之下,考虑特殊情况(比如特殊错字),可能得出更加符合事实的准确结论。
见过还是没见过
上一段中谈到的问题,又引出另一个问题。在阅读中,经常可以看到清人在校勘中引用某某宋本。得益于今天古籍数字化的发展,清人笔下的很多宋本已经比较容易的看到,于是问题来了,我们去核对,发现很多都对不上。前人说某宋本作某字,拿原书一核,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那么,前人到底见过其说的某宋本吗?或者他见到的宋本是我们今天所没见过的另一个宋本?这个问题还真不能用简单的是与否来回答。
在没有摄影技术的清代,想见一部真正的宋版书是很难的,大部分人见到的都是根据宋本校对而成的“校宋本”或者干脆就是“校勘记”,这些都以抄本的形式流传。明白了这些,就能理解在清人的校勘世界里,宋本(姑且用A表示)只是一个代号,他自己用的可能是由A衍生出来的复制品A1、A2、A3……,只不过被统称为A而已。举个不十分恰当的例子,我今天写论文,需要参考某本书,可是这本书在图书馆没有,或者已经被人借去了,或者我自己懒的不想去图书馆。于是我上网一搜,有这本书的电子扫描版,我参考它写成论文,但在论文脚注中仍说是参考了某书。其实我没见到过这本书的实物,但以今天的技术水平,我们相信扫描本的电子书和原书在需要传递的内容上是一模一样的。但古人看到的都是抄本,在辗转移录的过程中,免不了出现讹误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人笔下的宋本和我们看到的宋本有文字上的“差异”。
版本的“缺环”分析
讨论版本的过程中,大家都喜欢画“流程图”来说明版本之间的先后继承关系,这样当然没有问题,我自己也这么做。可是我们还要明白,古籍,尤其是宋元古籍,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,只是流传下来的很少一部分,在实际的古籍版本衍变过程中,并不是如A—B这样简单的发展。今天看到的只有A、B两个版本,而在实际版刻衍化过程中可能存在A—C—D—……—B这样复杂的演变过程,只发现A、B,不代表两者中间没有其他的版本如C、D等。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没法研究版本了,这里只是想说,一个真正有版本知识的古籍整理者,心中必须有这样的概念:版本的衍化,不是简单的A到B的过程。版本的研究,永无止境之路,今天的研究做的是符合今日条件的最恰当解释,假如有一天,有新的版本出现,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先前的研究。这种基于现有条件的研究思路,我老师将其定义为“版本缺环”下的讨论。
改字的原则
是古籍,就免不了错字;同样一本书的不同版本,也免不了有异文。整理的时候如何判定是非?如何掌握改字的标准?解决这个问题,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对校所能解决的,一个有版本素养的人,首先应当明白这些文字差异是如何产生的。
我老师常说,古籍文本演变有两大转折点,一是西汉刘向校书,而是宋代官方刊版。前者遥远,这里只谈后者,经过宋代官方的校刊,古籍文本基本上固定下来,进而随着抄本的消灭,后世版本的异文和唐代及以前抄本之异文有本质的区别。后代版本产生差异,除去错字,多数的异文,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唐抄本依据,而是他们根据其他的书更改了原有的文本。举我熟悉的例子,经部,据《经典释文》之改《礼记》;史部,据宋人校语(庆元本《汉书》所附)之改《汉书》,都是这种情况。
再举一个抽象的例子,某一个字,甲本是课本,作E。乙本是解释课本文句的字典,这个字作F(附音标[ef])。本来甲乙是两部不同性质的书,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异文也是很正常的,并且E和F字形很像,偶尔弄错了的可能性也是有的。
后来有一个“聪明书商”觉得把字典散入课本正文后会比较好卖,于是出版丙本,如果单纯合并作“E(F[ef])”,E和F应该是一个字,这样上下不相合,说不过去。字典有音标,大概错不了,只好大笔一挥,把课文改了,于是丙本的文本成为“F(F[ef])”。后来,再有一人,要根据丙本重新出版丁本,看了一圈,发现教育部核准的各省定本课文都是做“E”,课文事大,字典事小,再改成“E(E[ef])”。大家都觉得丁本比较好,但实际上丁本的文本是多次校改之后的结果,并且E的音标肯定不是[ef]。
其实,教育部颁定的课本一直以来正文都是做“E”,但字典呢,因为有音标的存在,发[ef]音的字可以确定只能是F(E的音标是[i:]),可见当时编字典的人看到的文本确实是作F,更加麻烦的是,这部字典也是教育部“钦定”的。其实原文到底是哪个字可以再研究,那已经超出了这里谈的版本问题。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,假如我们以甲本为底本,不能简单根据乙本改(两者性质不同,本非一书),更不能根据经过校改过的丙本改(经过校改的文字不可靠)。而单纯说甲本与丁本文本相同,也是没有考虑现有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文本演变。明白异文的来源、考虑它们曾经根据什么改过、这样改是否可靠,这些都是一个聪明的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结束
清人的版本鉴定,由于没办法寓目众多的善本,总体来看,主观的成分居多。现代科学的版本鉴定,由王国维及其弟子赵万里开创。尤其是赵万里,以北图馆员之特殊优势,比较众多善本,奠定了我们现代版本研究的基础,其所编《中国版刻图录》一书,至今仍然是有志于古籍版本学习的最重要选择。
限于篇幅,这里不再展开讨论其他比如原版与补版、覆刻与递修、刻工等古籍版本问题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上专门的课程,比如本学期历史系辛老师、桥本老师均开有版本课。如果非要推荐几部书的话,可以参考黄永年先生的《古籍版本学》、张丽娟老师《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》,尾崎康先生《正史宋元版研究》(中文版即出)等书。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,在讨论古籍刻工方面,目前最可靠的依据是《阿部隆一遗稿集》第一卷中附的《宋元版刻工名表》(此书虽无中文版,但日文版大部分是汉字,基本不影响理解)。啰哩啰嗦这么多,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古籍版本O(∩_∩)O
配图:北宋刻递修本(旧称景祐本)《汉书》
如果您喜欢我们的文章,欢迎与朋友分享!阅读更多原创文章,请